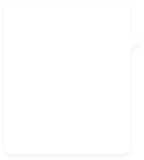犯罪成本不同于“案发前归还”,是指行为人在实施诈骗犯罪的过程中,为获取被害人的信任,加快犯罪进程,尽快实现犯罪既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关于犯罪成本能否从诈骗类犯罪的数额中扣除,应当重点关注犯罪成本对于被害人是否具有利用可能性,能否帮助其实现预期的交易目的,是否能够弥补其受到的财产损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简单地一刀切,一律扣除或一律不扣除都不足取。
一、犯罪成本和“案发前归还”的区别
犯罪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为实施犯罪行为而消耗的物质、金钱、时间、精神乃至生命的总和,即行为人为了顺利实施犯罪,实现犯罪既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以是否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和价值属性来衡量,可以分为物质成本和非物质成本;
而狭义的犯罪成本仅指物质成本,这种物质成本或直接表现为货币、金钱,具有明显的财产和价值属性,或表现为其他具有市场流通属性和交换价值的财物。
狭义的犯罪成本以支付对象是否是被害人来区别,又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反对给付。
直接成本以被害人之外的第三方为支付对象,是行为人为实施诈骗犯罪所必然产生的直接支出,如行为人购买作案工具、伪装道具,以及用于租用场地、交通工具和雇佣他人的支出等;
而反对给付则以被害人为支付对象,是行为人对受骗者交付的财产所提供的相当对价。本文所探讨的犯罪成本仅指狭义的犯罪成本。
所谓的“案发前归还”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刑法学概念,而是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一种习惯性表述,是指行为人在诈骗犯罪既遂之后、犯罪事实被司法机关发现之前,主动或被迫返还给被害人的物质利益,其与犯罪成本,尤其是反对给付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案发前归还”与犯罪成本所处的时间节点不同
归还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物归原主,属于事后返还,发生于诈骗犯罪既遂之后。也就是说,行为人应当先实施诈骗的实行行为,待实行行为终了,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实际控制财产之后,才有“归还”赃款(物)的可能。
如果行为人向被害人转移物质利益时,诈骗的实行行为尚未终了,被害人尚未处分财产,行为人没有实际取得对赃款(物)的控制权,且行为人意欲转移的物质利益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前提,则行为人这种先期给付物质利益的行为就不属于“案发前归还”,而是支付犯罪成本。
(二)行为人在归还赃款(物)和支付犯罪成本时所持的主观心态不同
“案发前归还”属于行为人在诈骗犯罪既遂后,对被害人所做的事后弥补,不论其初衷是否自愿,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行为人意图补偿被害人所受财产损失的主观意愿,其归还的目的主要在于修复被侵害的法律关系。
而犯罪成本是行为人为了顺利实施犯罪、使犯罪既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支付犯罪成本时,行为人的目的不是弥补被害人所受的财产损失,而是获取被害人的信任,加快犯罪进程,尽快实现犯罪既遂,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性。
(三)“案发前归还”和犯罪成本所针对的行为对象不同
“案发前归还”和犯罪成本都涉及物质利益的给付和接受,两者的给付主体一致,都是诈骗犯罪的行为人,但接受主体却有不同。反对给付与“案发前归还”都是行为人向被害人交付财物,接受主体是被害人;
而直接成本则属于纯粹的犯罪工具性支出,其给付的对象是独立于行为人和被害人之外的第三方。
二、认定“案发”的时间节点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认定“案发前归还”还应准确理解“案发”。
关于“案发”的含义,目前尚无明确、有效的法条依据可循。
有学者认为“案发”应理解为立案追诉,相应的,“案发前”是指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前。
另有学者认为,对“案发”可以做多种理解,如被害人报案、被主管机关发现、立案以及行为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但传统意义上的“案发”是指,案件事实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有关单位发现。
我们认为,从文理解释的角度来看,“案发”有两种含义,即犯罪事实发生和犯罪事实被发现。
如果将“案发前”解释为案件发生前或者犯罪事实发生前,则意味着“案发前归还”是指,行为人在着手实施诈骗行为之前就向被害人“归还”了“赃款(物)”。显然,这种解释不符合法条的上下文语义,颠倒了犯罪行为变化、发展的逻辑顺序,应予摒弃。
因此,可以将“案发前”理解为犯罪事实被发现前,确切地说,是行为人的主要犯罪事实被侦查机关发现前。
对此,可以参考1989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贪污贿赂罪解答》),该《解答》在提到挪用公款罪时指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未还’是指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未还。”
至于如何确定侦查机关发现犯罪事实的时间节点,我们认为,应以侦查机关初步掌握行为人主要犯罪事实的节点为准,确切地说,是被害人报案并提供证据证实可能存在被骗事实或者侦查机关进行了必要的初查工作并确定可能有犯罪事实存在的节点,不必将发现的时间节点严格局限于刑事立案。立案是刑事诉讼程序的起点,决定立案侦查当然意味着侦查机关已经发现了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此时,侦查机关对犯罪事实的存在表现出的是一种确定或者必然性的认知;
而发现可以理解为发觉,其在语言学上的含义是指,“开始知道(隐藏的或以前没注意到的事)”,发现犯罪事实在刑法学上可以解释为侦查机关初步了解了案件情况,意识到可能存在犯罪事实。
此时,侦查机关对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存在表现出的是一种或然性的认知。
从发现、察觉犯罪事实到决定立案追诉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也是侦查机关对犯罪事实存在的认知由浅入深、从或然到必然的必经阶段,立案只是这个认知过程的终点。
如果被害人在报案时能够提供线索或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基本的犯罪事实,则可以推定侦查机关开始知道存在犯罪事实,从而将这个认知过程的起点,即被害人报案并提供相应证据的时间认定为侦查机关发现主要犯罪事实的时间。
三、正确认识财产损失是处理犯罪成本的前提
诈骗罪属于财产犯罪,其侵犯的法益是被害人对财物的所有权或占有权,因此,在诈骗既遂的情形下,侵犯法益必然会导致法益受损。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从上述法条规定来看,“数额较大”是指行为人骗取的财物数额较大,并不直接意味着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数额较大。在此意义上说,似乎只要转移了数额较大的财物就成立诈骗罪。
但是,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诈骗罪也不例外,如果欺骗行为不可能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就不能成立诈骗罪。
所以,应当认为,诈骗罪的成立要求财产损失,被害人因诈骗行为遭受的财产损失也应纳入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做整体评价。
因此,诈骗罪(既遂)的基本构造可以简化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受骗者)产生(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
既然诈骗罪侵犯的法益是被害人的财产权利,那么诈骗犯罪的数额应主要反映被害人财产法益所受侵犯的程度,即应是一种被害人财产损失的数额,而非难以反映被害人财产损失程度的行为人获利数额。
因此,如何认定被害人所受的财产损失数额就成为确定诈骗犯罪数额的关键。
关于该问题,以德国法为代表的整体财产说认为,应当将财产的丧失与取得作为整体进行综合评价,如果没有损失,则否认犯罪的成立;在行为人向被害人给付物质利益的情况下,不仅要比较被害人交付的财产与接受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客观价值,还应重点评价该物质利益相对于被害人的主观价值。
而以日本法为代表的个别财产说认为,在如果没有欺骗行为对方就不会交付财产的情况下,由于交付财产是由欺骗行为所致,所以,交付财产本身就是财产损失。
从当前我国关于诈骗类犯罪的刑事立法实践来看,多部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都蕴含了整体财产说的合理之处。
如《申付强案电话答复》、1996年《诈骗案件司法解释》《金融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以及《非法集资案件司法解释》均明确规定,诈骗类犯罪的数额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已被追回或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2017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在第17点中也指出,“集资诈骗的数额,应当以犯罪嫌疑人实际骗取的金额计算。
犯罪嫌疑人为吸收公众资金制造还本付息的假象,在诈骗的同时对部分投资人还本付息的,集资诈骗的金额以案发时实际未兑付的金额计算。”根据上述规定,集资诈骗的数额=被害人交付的数额—行为人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该数额是行为人通过诈骗行为获得的“净利润”,从行为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其实际骗取的数额。
四、应当全面审查犯罪成本对于弥补被害人财产损失的有效性,再决定是否扣除
关于犯罪成本能否从诈骗犯罪的数额中扣除,我们认为,应当以整体财产说为理论基础,同时,重点关注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对被害人而言,是否具有利用可能性,能否帮助其实现预期的交易目的,是否能够弥补其受到的财产损失,再区别直接成本和反对给付做不同处理。
而不能仅仅因为犯罪成本是行为人为了实现犯罪既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主张一律计入犯罪数额,不予扣除,或者机械地比较被害人丧失和取得的财物的客观价值,不考虑利用可能性,只做简单的减法运算,一律将犯罪成本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具体而言,在存在反对给付的情况下,可以参考一般等价物扣减原则、同类物相抵原则和被害人目的符合性原则,全面审查犯罪成本对弥补被害人所受财产损失的有效性。
如果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对于被害人具有利用可能性,可以实现被害人预期的交易目的,能够有效弥补被害人所受的财产损失,则意味着支出该犯罪成本有助于恢复被侵害的法益,相应的,该犯罪成本所对应的财产价值应从诈骗犯罪的数额中扣除。
例如,行为人向被害人购买机床,承诺先期支付部分定金,待被害人交付机床后,再分期支付剩余货款。后行为人如约向被害人支付了定金,但其在收到被害人交付的机床后,立即将机床转卖给他人,并携款潜逃。
由于被害人交付机床的目的就是获取机床的对价,行为人支付的定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被害人的交易目的,弥补其因交付机床而受到的财产损失,故该定金应从行为人的犯罪数额中扣除。
如果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对于被害人没有利用可能性,无法实现被害人预期的交易目的,对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财产损失也没有实际意义,即使该犯罪成本有与被害人交付的财物相当的市场价值,甚至完全具备正常商品所应有的使用价值,也不应从诈骗犯罪的数额中扣除。
例如,被害人感觉胃部不适,去某黑诊所就诊,行为人是该诊所的医生,其发现被害人只是患有慢性胃炎,正常情况下,只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服药、调养就可痊愈。但是行为人却谎称被害人胃部有息肉、腺瘤,必须行APC手术(氩离子凝固术)切除患处,才能康复。
被害人为此向行为人支付了高额的手术费用,并购买了行为人推荐的术后康复药品。
事后,经权威专家证实,APC手术不适用于慢性胃炎的治疗。尽管APC手术是临床实践中确实存在的、有效的医疗手段,行为人推荐的药品也确实有助于被害人术后康复,但是对于只是患有慢性胃炎的被害人来说,APC手术和术后康复药品均缺乏利用可能性,购买上述医疗服务不可能实现被害人预期的“治疗慢性胃炎”的交易目的,无助于弥补被害人受到的财产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一律扣除犯罪成本会导致无法准确判断法益受侵害的程度,给确定犯罪数额带来不便,因此,这一类犯罪成本应不予扣除。
而在存在直接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人给付的对象是独立于被害人之外的第三方,无论该犯罪成本是否具有客观的市场价值、是否符合被害人预期的交易目的,因其对于被害人不具有利用可能性,被害人无法从该犯罪成本的支付中受益,行为人在客观上也就不可能通过直接成本来弥补被害人所受的财产损失。因此,这一类犯罪成本应当计入诈骗犯罪的数额,不予扣除。
关于犯罪成本应区分不同情况做相应的处理,目前也有明确的法条依据可循。
如关于直接成本的处理,《非法集资案件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于2018年11月9日颁布的《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在谈到诈骗数额的认定时也指出,“犯罪嫌疑人为实施犯罪购买作案工具、伪装道具、租用场地、交通工具甚至雇佣他人等诈骗成本不能从诈骗数额中扣除。”
关于反对给付的处理,该《指引》的相关规定则体现了一般等价物扣减的原则,即“对通过向被害人交付一定货币,进而骗取其信任并实施诈骗的,由于货币具有流通性和经济价值,该部分货币可以从诈骗数额中扣除。”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认定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首先区分行为人给付的性质是犯罪成本,还是“案发前归还”,如果行为人的给付属于“案发前归还”,因为有明确的法条依据,可以直接将其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如果行为人给付的性质是犯罪成本,则要进一步区分该犯罪成本是直接成本,还是反对给付,如果是直接成本,因为有明确的法条依据,应当计入诈骗犯罪的数额,不予扣除;
如果是反对给付,则要从犯罪成本对于被害人是否具有利用可能性、犯罪成本能否实现被害人预期的交易目的以及该犯罪成本是否能弥补被害人所受的财产损失等方面入手,按照上文所述路径做具体分析,再决定是否扣除。
文丨郑 毅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检察院